
原标题:在疫情后的世界里留学
2019年12月31日,因为飞机晚点了2小时,我错过了交响乐团的跨年演出。但是没关系,反正5月份我还要表演协奏曲,到时候我父母也会从中国飞来,听我在世界级的音乐厅展现我高中四年的最高音乐成就,看我作为学生会主席在毕业典礼上发言,见我与毕业舞会上西装长裙的朋友们一一道别留念......
三个月后,我第三次订的回国航班在波士顿机场起飞。机翼扫过熟悉了四年的跑道,在中途突然升起,毫无仪式感可言。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我高中的终点了,三个月前想象的场景最终沦为想象。
美高的完整体验,偏偏我们这届缺失了,想想也挺不公平。但仓促狼狈的乱局之间,想这种事没有一点意义。我用护目镜、防毒面具、防护服把自己包裹起来,在一半空位的客舱里,试着睡去。
在接下来的航程和隔离中,我再次思考了这次疫情的潜在影响,对美高、留学、乃至“国际教育”做了一些也许听起来不太主流的判断。
疫情后的世界:历史的重启与末人?
我出生的年份,是所谓“千禧一代”的第一年。这十几年来,中国经历了哪些发展,大家有目共睹。我不想给00后添任何刻板形象,但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文化潜意识中有一种乐观的的确定性。
这种确定性可以被粗略地总结为(但绝非全部):政治上不可逆转的多边主义、经济上不可逆转的市场全球主义、文化上不可逆转的(哪怕是狭义而肤浅的)宽容与多元主义 。
这些信念并不完全基于经验事实,而是一个时代意识共同体的产物,是一众学者和公知编织出来的一个普世信条。
其中,政治学家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在其《历史的终结与末人》中标志性地将冷战后的世界秩序称为“历史的终结”:“终结”并非是指历史事件不再发生,而是指再也不会有世界范围的重大意识形态变革,无论是政治、文化、还是经济上。
与90年代的多数学者一样,福山相信以上列举的三点是世界现在、20年后、200年后、2000年后的必然,时间已不再重要,因为历史已经不再演化。
这种对未来大趋势的确定性,即使不说造就了我们这一代的低龄留学潮,也至少定义了其性质。总结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这一代留学生很多不是为学技能、留在美国而留学。这点与上世纪末的留学生和一代移民的心态有很大区别。比起上一代留学生,如今留学美高的同学很少是以移民为目的,也就是说,没有强烈的意愿“出去”。
2、我们也不是清末的公派留洋生,没有迫切的“向西方学习,用以建设祖国”的目标。西方的优越性在新的国际秩序下成为了相对而非绝对的,一方面表明“西化”和“现代化” 早已成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另一方面也表明这一代小留学生“回来”的意愿也不强烈。
3、对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最终留在美国、回国、还是去其他几个国家,是个人选择,而大家也都相信,在美国受的教育能够支持他们作出其中任何一个选择。
这以上的任何一点,都高度依赖现有的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政治合作多边化。
比如,正是因为全球贸易在当下的全球化下是一个相对开放、共通的整体,留学生才有信心他们在美国的学位可以被远在大洋彼岸的公司认可:规则是共通的,在哪里学都可以。
正因为当下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美国社会都相对允许多元化文化,小留学生才能放心地住在美国的住家,同时相信他们留学的经历不会在回国后成为原罪。在美受歧视、回国不适应已经被视为异常而非常态。
我们留学现状所依附的条件,在疫情后的世界里也许是脆弱的。
从疫情期间留学生的处境,能够正常的看到一些端倪。我们中的很多人,匆忙回国并非完全是为了回避病毒本身,而是逃离那已经在发生、潜在发展迅速而猖狂的种族暴力。
从一开始听说遥远的欧洲殴打留学生事件,到纽约亚裔戴口罩被推下轨道、再到我本人在波士顿被吼“滚回中国城” (Go back to Chinatown),种族暴力事件对很多留学生而言已经从新闻上的传言变成了亲身经历的恐慌。
而这种将疫情发展为种族问题的做法之来源不是别人,正是美国总统。正如Chinese一词有“中国的”和“中国人”两个翻译,特朗普著名的Chinese Virus也有“来自中国的病毒”和“中国(人)病毒”两重意义。
这种种族沙文主义背后的文化不宽容,在中国体现为对留学生回国的敌意。只需上微博搜索“埃塞俄比亚中国留学生滞留”,从一众评论就可看出, “祖国建设跑老远,千里投毒排第一”这种情绪绝非仅是互联网上的少数个体。
此类言论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但每一个都是直接或间接建立在“中国vs外国”这个愈演愈烈的二元对立上的。留学生所经受的遭遇,反映出的是两国相当一部分人对彼此的看法。
疫情后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不是我一个高中生能够预测的。然而,各派学者的共识是,上世纪下半页以来的政治、经济全球化,在疫情后必将有相当大程度的改变。除了企业归岸国内、限制人员流动,和退出国际组织、放弃多边交流等看得见的举措,民众对全球化的态度也将向怀疑和悲观转变。
并不是说此章节开头提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三个条件会因疫情而完全消失,但那“乐观的确定性”也许就会有变化了。历史也许还远远没有终结,而此次疫情也许正是其重启的开端。
福山“末人”的概念源自尼采,描述满足于安定与物质享受而随波逐流、不敢冒险的大众。然而,似乎正是这群被视为“历史终结”重要组成部分的末人,正在通过其对未知的恐惧(排外民族主义)、对风险的回避(供给链冗余理论与企业归岸)、以及随波逐流(民粹主义)将历史终结论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在国际政治中留学
“并非所有的危机都是转折点” 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察·哈斯发表在最新一期《外交》文章的副标题。哈斯相信,此次疫情的影响其实是加剧了存在已久的国际政治格局,而不是彻底地颠覆目前的秩序。
疫情并非真正“导致”了其后续的问题,仅仅是让已有的问题更加凸显而已。这并非是一个乐观的预测,因为哈斯所谓的“存在已久的国际政治格局”,可以用身份政治和现实政治两个概念来概括。而这两个概念中的任何一个,对“留学”与“留学生”的接受程度都是不确定的,而近些年的重大事件又似乎完美应和了这两个理论。
身份政治理论的代表作,就是北美高校每一个政治学大一学生都读过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塞缪尔·亨廷顿在此书中提出了“文明冲突论”,用于反驳他学生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虽然当今身份政治理论远比亨廷顿设想的更复杂,但其基本原则是不变的:身份和文化认同作为一种政治需求和政治力量,比意识形态、普世价值百科强有力得多。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就是这种政治需求和政治力量的体现。
从公开的反移民政策,到同样公开的歧视少数族裔,再到“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第一”等口号,特朗普的魅力之一便是他对美国白人的特惠和对任何其他族群的排斥,而无数红脖投票给他的原因也是他公开的种族主义让红脖感到了“白人”这个身份的归属感和优越感。
而有这种想法的人有多少呢?答案:多到足够让特朗普赢得总统竞选。
英国脱欧,证明了民族身份认同还可以颠覆一体化政治经济体系。虽然英国一直以来对欧盟的经济、社会福利政策就称不上忠诚的支持者,但是真正导致脱欧的最根本原因是近10年以来的欧盟开放国境政策导致的难民输入。
英国同美国一样,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发源地,是当我们提到“西方”时第一个想到的国家,然而如今英国有足够多的人口因为对外来民族的敌意,而选择彻底放弃欧盟这个政治经济一体化组织,在经济上自断臂膀。
另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就是我们听了太多遍而已经不自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细想起来,这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异曲同工。义务教育中 “中华民族 vs 列强”的二元对立近代史观,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只是需要硬着头皮背的知识点,但对更多人来说,这已确定进入到了其文化潜意识中,形成了如今很大一部分网民信奉的“中国 vs 外国”二元对立,直接导致了对留学生回国的冷嘲热讽。
所谓现实政治,就是以国家(而非民族、意识形态等)为政治的基本组成单位,做博弈论式的理性决策分析。
关于中美关系的现实政治分析,代表人物莫过于中美首次建交的始作俑者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现实政治学派的掌门人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启一带一路计划并开始实质性地挑战美国主导的经济政治秩序,美国智库界对基辛格和米尔斯海默理论的讨论愈来愈活跃。米氏偏悲观,预测中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基氏偏温和,认为通过对双方核心利益和需求的了解,中美并非存亡之敌。
然而,俩人理论的共同点在于,中美敌对关系的原因既不是意识形态之别,也不是任何其他单一的事件或因素,而是战略上的:两个强国的存在本身,就足以是它们矛盾的缘由。因此,这种矛盾在本质上是不可化解的,只能如基氏所说的去淡化(避免军事冲突),或者如米氏所说的去斗争,直到其中一方被削弱到对另一方不构成威胁。
用这个悲观的现实政治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长久以来的媒体舆论战。今年3月10日,纽约时报在20分钟内,先后在官方推特帐号上,报道了中国和意大利两个国家为抗击疫情而下达的的封城政策。然而,同样的政策,发生在中国便是侵犯人权、“损害人们自由与生活”,在意大利便是英雄般的“牺牲经济阻止疫情蔓延”。
类似的双标报道,其实在主流美媒上一直以来就不缺:但凡是中国发生的事,非廉价劳动力即污染,要不就是反人权。
我相信很多留学生同我一样,在出国前对美媒的客观性有过信任,也发自内心地欣赏“自由媒体”这个理念。但是在美国生活过就会发现,常在媒体上读对中国报道的同学,他们不会区分远在大洋另一端的那个国家和近在眼前的这个个体,对中国这个国家的认识和偏见最终都转化为了看待留学生时戴的有色眼镜。
当然,这不是说美国同学无知。试想,在中国又有多少人能客观、理性地看待美国,并拒绝使用“美国”、“美国人”这种想象共同体来判断那一个个持蓝色护照的个体?人性使然而已,不必强求。
而之所以中美媒体如此专注于抹黑对方,正是因为其战略敌对关系,而当“自由媒体”的理念和国家利益的现实直面相对,理念必然退让,也已经无数次地退让。
这次疫情对留学生最大的影响,也许并不是广泛的停课和回国逃疫,而是我们突然间意识到: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从一个推崇国际背景、高度互联、缓慢却坚定地走向消除误解和冲突的世界,变成了一个种族认同、文化冲突和现实政治的角斗场。
以往留学生仅为提升英语、参与模联而读的国际政治新闻,如今却突然近在眼前,真实地影响着这一代留学生的未来。
低龄留学与国际教育:但丁之堕落天使?
但丁在其巨著《神曲》中描述了这样一番景象:一群平庸的幽魂、堕落的天使,曾不忠于上帝,但也不敢反叛,被驱逐出天国之外,却也入不了地狱,只得游荡在地狱之门前,进退不得。
这个“进退不得”的状态,就是低龄留学生的文化认同现状。
美高、美初留学生不似本科、研究生留学生,后者不仅志学之年大多在中国度过,其留学的目标也多半仅仅是学习知识和技术,无论是用来回国应用还是留在美国成为第一代移民,其文化身份都有明显的中国特质。
而美高、美初留学生也不似华裔,后者以美国为家,未来也不太可能回到中国。对低龄留学生来讲,虽然更早的接触对了解美国社会有帮助,但往往离真正融入还有差距,而同时,这关键的几年又使得中国这个“家”成为一个模糊的概念。
这种模糊感在本次疫情中尤为强烈。当4月10日第一架包机抵达纽约机场撤离在美小留学生时,不知道机上的孩子有何感受:一方面,登上眼前的飞机就能回家了,另一方面,他们在微博上已经见了太多不欢迎他们回家的舆论;一方面,家里的管控和规则保证了疫情下的安全, 另一方面,他们也许已经不习惯这些规则。
创立美高学长帮的半年来,我有幸接触了许多重视并选择了国际教育的家庭,其中很多家庭对孩子教育的重视让我由衷地感到佩服。
孩子幼儿园就在英语授课的国际幼儿园,小学开始便在世界各地的国际学校就读,初中便申入英美最顶尖的私立初中。
在这样教育环境成长的孩子,很难不精通多门外语、兴趣特长满身、擅长一两项体育运动,既优秀又有趣,是顶尖美高最青睐的申请人。
然而,比起这些可见的技能更吸引家长的,是国际教育带来的国际视野、国际背景,这些似乎是能让孩子受益终生、始终赢在起跑线上的软实力,其重要性是不可度量的。
但是,据我半年来的观察,我发现国际教育,不管是理念还是现状,都有一种方向上的盲目性。
首先,选择国际教育是一张单程票,一旦从幼儿园选择了国际教育,孩子就与中国教育、和他们绝大多数同龄人的共同体验绝缘了。
中国教育还是国际教育?是一个家庭的选择,理论上怎么选择都无所谓。然而我发现,其实很多家庭并没有做好做出选择的准备,在孩子选择国际教育后,才开始担心孩子丧失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了解,进而给孩子原本就过于丰富的课业、课余活动再添一个中文辅导班。
这种焦虑的背后,是对孩子未来文化归属的不确定。很多家庭并不准备让孩子彻底脱离中国,甚至计划未来让孩子回到中国,想让孩子的国际背景在中国发挥作用,然而要知道,两全其美的事永远都是少数。
知乎上“如何看待留学生回国避险”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一个热门回答,引用了英国报人David Goodhart的一个概念,叫做 “Somewhere people vs. anywhere people”(有根人vs无根人)。
这个回答的核心内容是,虽然大多数人出于种种原因而不可离开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有那么一群人可以无视国界、无视文化差异地随处安身,因为他们的资源和技能使他们随时可以流动,并且他们没有“归属感”这一说。
也许很多家庭选择国际教育、选择让孩子低龄留学的初衷就是想让孩子成为后者,成为四海为家的 “无根人”,成为无论在哪里都能成功的精英。
然而,正如我上文所说,这一代留学潮、国际教育潮非常大程度地依赖于我们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
这个定义了我们这代留学生的理想条件,已经在过去的几年中不知不觉地被侵蚀,而这次疫情仅仅是将事实更露骨地甩到了我们眼前而已。
这么说来,以美高生为代表的低龄留学群体、以及以美高为模版的国际教育模式,在疫情后的世界里,也许情势并不乐观。
结语:
预测未来,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事实上,我写了这么多字,根本没有真正地“预测”留学的未来,只是用几个学者的理论去试图理解几个事件,并和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一下我发现的趋势而已。
我不是说疫情后就没有低龄留学了,或者说低龄留学会变得危险,我甚至都不是说低龄留学热度会下降或是上升。我只是说,我们目前的这一种低龄留学的特征、动机和目标,是高度依赖我们一直以来的国际局势的,而这国际局势本身已经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其改变带来的影响在疫情之后也许会突然显现。
这影响,对有些人来说是积极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是消极的,取决于每个个体的处境和目标,我不能一概而论之。
写给低龄留学群体的同时,这篇文章也是写给我自己的。
我时常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个有趣的时代、一个可能会见证历史的时代,但随着一件又一件见证历史的事发生,我反而麻木了,逐渐放弃任何对大过自身之事的思考,沉迷在日复一日的忙碌和竞争中。
这次疫情在某种意义上点醒了我,让我第一次真正地意识到,我的生命是有限的。我可以按照计划,在芝大选一个职业化的专业,做竞争最激烈的实习,毕业后输送到某券商、某律所 (事实上我可能也真的会这么选择),但这是一条所有人都能走的路,它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独有的经历漠不关心。
历史仍在继续,而我们也许正处在一个十分有趣的转折点,我即使不能参与其中,若连试图理解它都不去尝试的话,岂不是太可惜了。
责任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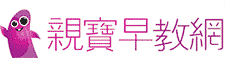

 早产喝什么奶粉好早产儿奶粉使用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早产喝什么奶粉好早产儿奶粉使用的注意事项有哪些 4个半月的宝宝吃奶量宝宝吃多少奶更为健康合理
4个半月的宝宝吃奶量宝宝吃多少奶更为健康合理 早产婴儿治疗费用可以报销吗早产婴儿治疗费用报销流程介绍
早产婴儿治疗费用可以报销吗早产婴儿治疗费用报销流程介绍 4斤的早产儿怎么穿衣服如何挑选适合宝宝穿的衣服
4斤的早产儿怎么穿衣服如何挑选适合宝宝穿的衣服 新生婴儿要用什么枕头如何为新生婴儿选择合适的枕头
新生婴儿要用什么枕头如何为新生婴儿选择合适的枕头 新生儿溶血症换血疗法是什么怎么预防新生儿溶血症
新生儿溶血症换血疗法是什么怎么预防新生儿溶血症
